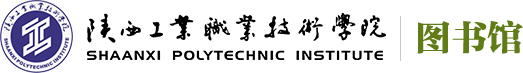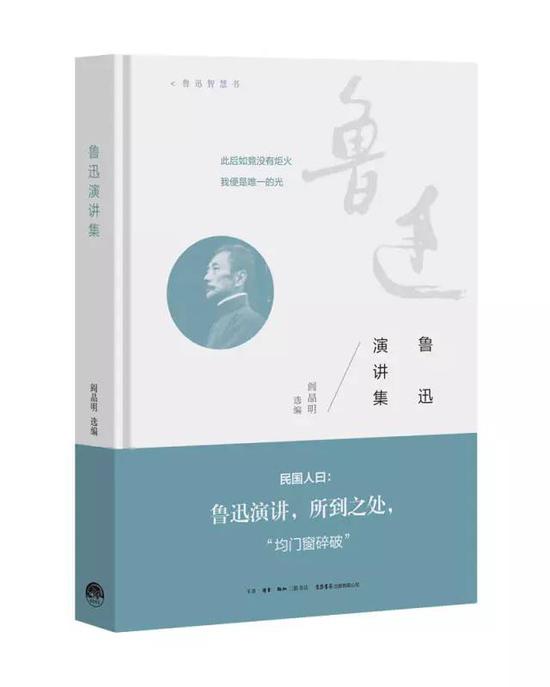 《鲁迅演讲集》 阎晶明 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7年3月
《鲁迅演讲集》 阎晶明 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7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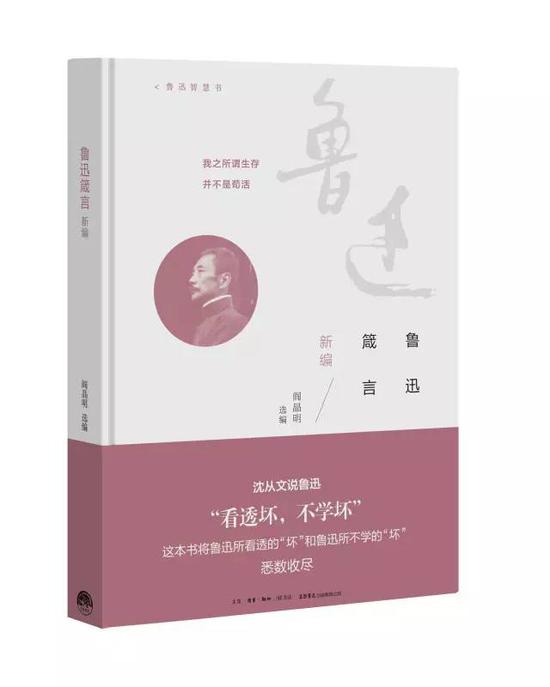 《鲁迅箴言新编》 阎晶明 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7年2月
《鲁迅箴言新编》 阎晶明 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7年2月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批评家阎晶明选编的《鲁迅演讲集》《鲁迅箴言新编》。其中,《鲁迅演讲集》由“上编”、“下编”、“附录”三部分构成,收入了鲁迅先生影响深远的诸多演讲篇章,《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演讲》《读书与革命》《文学与社会》等均在其中。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和青年导师,他的启蒙理想,表现为毕生致力于使中国的年轻人开启智慧,洞察社会,少走弯路,提高对生活挫折的耐受度,完成有建设性和创造力的人生。因此,对于读者而言,鲁迅的启蒙思想极富营养。而鲁迅的启蒙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他面对青年和后学之辈的演讲当中。因此,鲁迅演讲的特殊价值,由此可见一斑。编者将鲁迅先生的演讲单独结集,并加以精要的点校和解读,提供了鲜活的现场感,更具丰富的史料意义。
《鲁迅箴言新编》将鲁迅先生的“名言”分15类呈现在读者面前,包括“论斗争策略”、“关于国民性”、“对中国文化之判断”、“对文学艺术的见解”、“青年的使命”等。在谈及选编本书的缘由时,阎晶明写道,“本书的目标不是想编一本可以省略阅读《鲁迅全集》的工具书,真正的目的,或许倒是引起读者阅读鲁迅文章的兴趣,借这些片段摘录而去查到鲁迅原文去整体阅读⋯⋯我愿以此冒险的工作,来表达对一位中国现代的伟大作家的致敬,也希望读者能从中理解和了解到他的伟大,激发起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探索热情,引发出更多关于人生世事的思索和理解。”
从鲁迅谈演讲魅力
(以下内容选自阎晶明新书《鲁迅演讲集》)
鲁迅是演说家,他有证可考的讲演达六十六次之多。鲁迅本人并不喜欢到处讲演,“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海上通讯》)。他的讲演大多是因为无法拒绝邀请者的“坚邀”而不得已为之。鲁迅讲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语调也不高亢,他的话并不能为所有的听者全部听懂。然而无论在北京、厦门,还是广州、上海,凡鲁迅讲演的时候,听者的热情都格外高涨,目睹鲁迅风采是很多人前往聆听的主要原因。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自上海回到北京探亲,期间他曾应邀到北大等大学讲演。据当时报载,在北大讲演时,“距讲演尚差一小时,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已人满为患”,主办方只能改至第三院大礼堂,听者于是蜂拥而至,最终“已积至一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回到北京,在北师大讲演时,由于听众太多,不得不改到露天操场进行,听众达到两千余人,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的讲演常常是到了现场才道出主题,他的讲演在并不展现“技巧”、显示“口才”的情形下,却令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之激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思想,讲真话的要求,直面现实的胆魄,等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构成鲁迅讲演魅力的根本原因。但就站在“学者、作家及其讲演”这个话题上讲,我以为鲁迅讲演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讲演的真正魅力不在于现场的绘声绘色的表演,不在于滔滔不绝的“妙语连珠”,而在于讲演者在讲演背后作为作家的创作和作为学者的研究是否真正可以为其“立言”。讲演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靠文章说话”。
我们说鲁迅是演说家,但上述那种讲演盛况对他而言并不是从来就有。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进京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刚刚履职的第二个月,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夏期讲演会”,邀请中外学者就政治、哲学、佛教、经济、文化等作讲演,鲁迅被聘讲演《美术略论》。根据鲁迅日记记述,他总共去了五回,讲了四次,讲演的情形却并不令人乐观。六月二十一日第一讲,“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二十八日作第二讲,日记没有记载听讲情形;但第三次,即七月五日,鲁迅冒着大雨“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十日,“听者约二十余人”。最后一次即当月十七日,也是雨天赶去讲演,“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五次赶场,听者总人次居然不过百,情形之冷淡可想而知。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恐怕是必然的,那时的鲁迅还只是初来乍到的“公务员”,以学者的身份前去讲演,号召力显然不足。到二三十年代,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再去讲演,盛况之壮观每每令人惊讶。在所有的原因当中,我最想说的,是鲁迅靠的是文章立言,没有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方面的创作,没有他在小说史上的研究,没有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果,讲演又何能谈得到令人期待?我们今天的很多演说家,越来越走“专业讲演”的路径,学问没有根本,研究难得钻研,创作上未必有什么成就,却忙着上电视、进礼堂,侃侃而谈,不亦乐乎。最终让人看破真相甚至令人厌倦,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夸张的姿态,油滑的腔调,故作的高深,随意的解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在回避一个作家、学者立身的根本,遮蔽学术讲演立言的根基。
讲演的号召力不是或未必是言说本身,讲演的魅力来自更为深沉的、丰富的底蕴。林曦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听鲁迅讲演时的感受,我以为他的描述特别能表达我自感难以言尽的观点:“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么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林曦《鲁迅在群众中》)
讲演者的信心来自讲坛之外的地方。
识箴言更须读全集
(以下内容选自阎晶明新书《鲁迅箴言新编》)
动手编一册关于鲁迅言论的书,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十多年前,我开始收集有关“鲁迅语录”的书籍。这类书又以文革时期印制的最多。说是印制而非出版,是因为其中大部分书并无正式出版单位,多是当时的大中学校学生小组、工厂里以车间为基础的工人小组甚至红卫兵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编辑印制的,发行范围已不可考,但“语录体”的状况却是差不多的。
翻阅这些书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作家里只有鲁迅可以“语录”?为什么鲁迅语录可以按照任何时代的政治要求、文化氛围来编辑?更深入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一句鲁迅的话,或一个文章片段,可以在不同的条目下放置,从而看上去并不完全“牵强附会”?这绝不纯粹是一个文学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极致层面上,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鲁迅的话语具有“超级不稳定”结构,或极具模糊性、流动性的特点?我们能不能从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对鲁迅的语言、文体和表达风格做一次学理上的分析与研究?我所指的是,在我看到的“鲁迅语录”里,大家都可以按照“阶级与阶级斗争”“打倒孔家店”“反对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等条目,去鲁迅杂文里找到对应的句子或片段。这些语言仿佛并非条目所指,又仿佛确实与此相关。
我想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作家来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大多直指主题,具有极高的确定性,一句评论时事的话,一种评论社会现象的表达,如果那时事已经消失,那现象也成为旧事逸闻不复存在,与之相关的文字也就失去了效用,扩散的幅度随之增减。鲁迅却是个例外。
但这绝不是一个人可以一时就能解决的学术问题,我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却深知自己无力面对。最后,这些想法就逐渐简化成为编一本自己挑选、自己分类的“鲁迅语录”。因为即使加上文革后编辑出版的同类书籍,我以为我们面对鲁迅名言时往往有一种选择上的趋同,这就是,我们仍然按照鲁迅评论社会、历史的态度寻找其中的“硬性”话语,而忽略了他同时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许多论断是针对文艺问题的,他还有很多关于生活、关于个人、关于人生的议论不但有妙趣,而且惹人思。他的言论应该在更大范围、更全面的领域里被人认识。
范围还不是最重要的,理解鲁迅一段话真实、完整的意思,必须要阅读他的全文,而理解他某一篇文章的意旨,又应当对他整个的思想有所认识。但同时,鲁迅文章的复杂性是分层面的,即使你不能理解他的深刻用意,却并不妨碍你欣赏他的美文。你摘出来的鲁迅名言也许有——通常一定有——比文字层面更深刻更复杂的内涵,但即使就按照你所理解的那样去引用,大多数时候又仍然是有效的。这真是个奇妙的现象。
我们对鲁迅的误读,常常是发生在两点上:认为鲁迅的“曲笔”是难懂的;认为鲁迅的批判就是刻毒的骂人和一个都不宽恕的回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觉得有必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编一本鲁迅语录。
由于鲁迅是专注于解剖中国国民性的,所以在他笔下,不管是小说里的灰色人物,杂文里的学者名流,其实都不只是他个人和他那一阶级的代表,他们都具有“国民性”的通病和共同特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他文章的意旨。他讨论任何问题,哪怕是一封给朋友的书信里探讨一本书的编辑问题,也常常会发出题旨以外的感慨,所以收集鲁迅名言不能只到他的名篇里去找,而要寻找“日记”之外的所有文字。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力量,这就是鲁迅文字的魔力。因此,既然自己反复阅读了这些文章,或有必要为读者做一点总括性的事情。
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再次阅读了鲁迅所有的文章。我深知,尽管如此,自己的编辑也是很难到位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将自己认为属于“鲁迅名言”的文字划出来,将划线部分全部摘录完毕后,再回过头来挑读他的文章,发现,那些未曾划线的部分里仍然有大量精彩的论断。但既然是语录,总会有取舍。我就硬着头皮把本书编成了。它们绝不能说代表了鲁迅言论的精彩,更不能说集中了鲁迅思想的精华。他们永远是不周全的。理解鲁迅,惟一的办法是阅读《鲁迅全集》,而且是一遍又一遍地进行。
这是不是有点神话鲁迅?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我尽量在编辑条目上力图清晰。本书的分类共15种。其中既有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中国文化的批判,也有对文学艺术、中国新文学的分析,既有对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的态度,也有对自己作品的自谦或辩护,既有对青年、对同时代人的思考,也有对中国社会情状、对人生的理解。选择和分类时,首先注意捡摘句子时的把握,每论需尽量寻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话语,即虽然鲁迅论述的是一时一事,但话语却可指涉更广大范围。比如对同时代人的评说,鲁迅文章里涉及到的人名太多了,我所取的,是当他评说某一人时,也指向了对某一类、某一阶层人的态度,比如他关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三位人物韬略的比较就非常有趣而典型。其次,在分类上难免勉强,因为正如前述所谈,鲁迅的话语具有不确定、不稳定的特点,具有模糊性、流动性的色彩,谈国民性时也是谈美学问题,谈艺术时也涉及民族特性,谈青年也是谈人生,谈人生又何尝不是谈艺术。我在分类选择时,重点是看文章整体的用意和主题,文字里直接的取向和针对性。第三,所选的话语尽量保证原文的完整性,既要保证“名言”之精彩、精练,又不要随意断章取义,尽量从句号后面开始摘录,一直到以句号为“休止符”。但也有时不能完全做到,有时就在逗号处开始或结束。有时是我自己在结尾处将原文的逗号改为句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这样的情况尽量少之又少。
本书的目标不是想编一本可以省略阅读《鲁迅全集》的工具书,真正的目的,或许倒是引起读者阅读鲁迅文章的兴趣,借这些片段摘录而去查到鲁迅原文去整体阅读。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用意是否恰切,能否达到那样的目的是不敢断定的,也因此,我希望,即使就本书内容而言,也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鲁迅、对鲁迅所评说的人与事的认识。
我以此冒险的工作,来表达对一位中国现代的伟大作家的致敬,也希望读者能从中理解和了解到他的伟大,激发起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探索热情,引发出更多关于人生世事的思索和理解。编者所愿若能实现十分之一二,则亦为幸事。
作者简介:
阎晶明,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出版有《鲁迅的文化视野》《鲁迅与陈西滢》等著作。在《鲁迅研究月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等发表多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及学术随笔。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